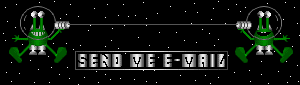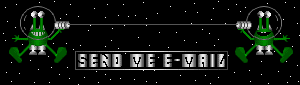本文寫作於1997年,今日的電腦網路科技已經不一樣了! 幾年前,我走進一個無形的網,從起初的盲目摸索開始,到現在的隨心所欲、來去自如。遊走的據點越來越多,活動的範圍越來越廣,我也和許多人一樣,一走進這個網,體會了它的好處,就越來越離不開。
這個網是無數人投下許多時間和精力才織就的,這些年來,它的領域擴充、變化的速率令人難以想像,它所代表的,是無限的可能。你可以安穩地坐在網中央,只要一個指令,你所需要的資訊就可以從世界各地湧到你面前……這就是越來越多現代人加入的網際網路。 由於唸書和工作的關係,我開始接觸到網路,幾年下來,在電腦和網路方面學到了不少東西,儼然成了許多人眼中的「專家」。其實,我只有半桶水的份量,好用來唬人,頂多只算是砌俄羅斯方塊、掃地雷和打磚塊的「磚家」而已。
但也靠這半桶水的功夫,我雖然離家這麼遠,一個人在澳洲,卻不覺得寂寞,因為同學總會請我幫他們解決電腦問題,而他們就幫我蒐集寫報告要用的資料,我在電腦公司的工作也越做越順手,幫了不少顧客和朋友安裝了網路,帶著他們走進一個沒有邊界的領域——而那領域,充滿了太多超乎想像之外的驚奇…… 馬克是經過我同學安德魯的介紹,才會來找我,幫他父親賈克.巴鐸先生買電腦。由於安德魯大力鼓吹「SOHO完全電腦化解決方案」的好處,他們除了電腦外,還添購了許多其他的週邊設備,例如
以數據機取代老舊而畫質不佳的傳真機……等等。
因為巴鐸先生常要傳真或郵寄文件到加拿大,我便建議他問對方有沒有電子郵件的設備,如果有的話,就可以用這個方式傳送文件,可省下不少電話費——他很高興地接受了我的建議,成為網路世界的一員。
馬克原來在學校就有使用網路的經驗,但從來沒在家用過,見到父親用的新系統功能這麼強,就要求我也幫他安裝,這樣的話,他就可以直接把平面或動畫作品傳送給他的公司,不用委託快遞公司或是親自跑一趟——沒想到他走了進去之後,卻好像上了毒癮一樣,再也不肯出來。 我一直無法了解馬克是個什麼樣的人,如此難以捉摸。其實他長得挺好看的,麥色的皮膚,略長的深棕色頭髮,瘦削的臉上帶著些鬍渣,加上說不清是什麼顏色、迷迷濛濛的眼珠,很頹廢的感覺——那是他給我的第一印象。
但他一開始說話,我就發現他是個思維清晰、條理分明的人,對他的看法立刻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。
馬克也在我們那所大學修課,算來是我和安德魯的同學,但他是設計學院的,在另一個校區,如果不是因為幫安德魯的公司做美術設計的關係,和我們商學院的根本沒什麼機會碰面,更別說會認識對方了!
說來也是在安德魯連哄帶騙之下,堅持要我親自出馬,到巴鐸先生家安裝電腦設備,才會和馬克父子熟悉起來的。而他利用護送我去工作的藉口,帶著女友莎拉到兩百公里外的海邊歡渡週末,只要兩個鐘頭的工作,卻讓我留了兩天,這筆帳
,我還沒跟他算呢! 安德魯開著他那部四輪傳動的大車來接我,一路上邊開車邊講個不停,還不時轉過頭來對坐在後座的我做鬼臉,把我搞得心驚膽跳的,又不好意思叫他專心開車——可是看坐在前座的莎拉,卻是面不改色,真是服了她!
到巴鐸先生家的時候,我總算鬆了一口氣,飛也似地跳下車。巴鐸家是一幢漂亮的白色房屋,在一片翠綠樹林的圍繞之下,那白色顯得特別明亮。
馬克開了門,帶我去客廳,有個高瘦的中年人站了起來,短而鬈的灰髮,明亮的綠眼珠,馬克說這就是他的父親,我只覺得他們父子長得實在不太像。
在安德魯和馬克的幫忙之下,我們很快就把所有的電腦設備裝好,線路接上——其實大部分安裝和測試的手續原來在公司就已做好,他們只要把東西接對地方,電源打開就行了。但安德魯卻要我大老遠來,在巴鐸先生面前親自示範所有硬體軟體的使用方式,真是受不了!
其實,巴鐸先生也只不過買了兩部電腦,一部數據機、雷射印表機和掃瞄器而已。一部電腦是給他自己用,另一部是給他的助理使用,她一星期只來三天。兩部電腦有網路連接,可以立刻使用對方的檔案或其他的週邊設備。
安裝完成,巴鐸先生請我們到樓上陽台喝茶。我一走上陽台,立刻被眼前的景物迷住了。這房子地勢高,向遠處望,可以見到左方和右方都有一道山崖——就像一個人伸出兩臂,把桌上的東西攬進來一樣——形成一個海灣。這海灣有許多奇形怪狀的岩石,還有兩個白色的小沙灘,除了海
與天的藍、岩石的黑,以及沙灘的白之外,就是深深淺淺的綠……
那景色,比起渡假旅館的窗景,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,這時我才知道安德魯這麼喜歡來這裡的原因。我望著眼前的景色出神,直到巴鐸先生問我要喝茶還是咖啡。
我們五人坐在陽台上聊了起來,之前我已知道巴鐸先生是個作家,也幫一家加拿大的出版社做些編輯的工作,這時我好奇地問他都寫些什麼,他先是神祕地笑了一下,啜了口咖啡,才說是恐怖小說。
「真難想像,這麼溫和親切的人會是個恐怖小說作家。」我恭維他。
「我也很難想像,這麼年輕的漂亮女孩會是個電腦專家。」他也回敬我。
我心裡想,我才不是什麼專家呢!而且他們哪看得出我們東方人的年齡和相貌?但我還是哈哈一笑,道了聲謝。 喝完茶,本來我應該開始向巴鐸先生示範電腦和其他設備的用法,但他卻要我和安德魯他們一起出去走一走,電腦的事晚上再說。
馬克帶路,安德魯、莎拉和我跟在後面,穿過濃蔭的樹林,走了二十幾分鐘,眼看著就要沒路了,沒想到轉了個彎,卻是一片海闊天空的沙灘——安德魯和莎拉不禁歡呼尖叫,一邊跑一邊脫去外衣,露出穿在裡面的泳裝,東西一扔,手拉著手衝向海裡。
馬克則慢條斯理地脫了衣服,才跳進浪裡游了一會兒,便又起身穿上衣服陪我散步。我沒準備下水游泳,只脫了鞋子在淺海裡走來走去,好好地欣賞周圍的景色,沒想到偌大的海灘只有我們幾個人享受。馬克告訴我,知道這地方的人本來就不多,剛好那天有足球比賽,所有的人都看球去了。
到了晚上,我們到所謂的「市區」吃完所謂的「中國食物」,再回到巴鐸先生家時,巴鐸太太也回來了。她在一家大醫院做行政工作,一頭紅髮,身材高而苗條,看起來很年輕。她對人熱情得不得了,堅持要我們叫她蜜雪兒,一見到莎拉和我就又抱又親的,我被她親得心裡有點發毛,不知道她是不是對病人也這個樣子?
我的眼光掃過巴鐸先生、蜜雪兒和馬克,真不明白,他們的長相和性格怎麼會差那麼多?一家三口,三種截然不同的類型。
馬克和安德魯他們帶著東西去夜釣,我則隨巴鐸先生到他的書房,繼續我的工作。我完成示範之後,便請巴鐸先生坐到電腦前,問他還有什麼問題要我解答,然後開始練習。
「你一定覺得很奇怪,為什麼馬克和我一點也不像。」他拿著滑鼠點了幾下,突然說。
我其實並沒有問的意思,但他既然開了口,我也很樂意聽故事。
「他不像我,他像他的母親。」 賈克.巴鐸是法裔加拿大人,二十幾年前到歐洲旅行的時候,在希臘邂逅了一個美麗的女子,雙雙墜入情網,他在希臘逗留了幾個月,決定結婚,然後帶她回到加拿大生活,她很快就有了身孕。
但希臘女子一直無法適應加拿大的天氣和生活方式,又想念希臘的親友,健康情形越來越差,情緒也極不穩定,加上和巴鐸先生文化背景的差異,婚姻生活開始有了問題。馬克三歲那年,她回希臘探親,所有病苦居然不藥而癒——大概是中國人所謂的水土不服吧?後來她就沒再到過加拿大。
分居後,巴鐸先生的狀況並不好,自顧不暇,馬克有個姑媽自告奮勇地接馬克回家照顧,巴鐸先生則每週去探望他幾次。姑媽對他很好,卻在馬克八歲那年死於癌症,巴鐸先生那時經濟情況已有改善,便他帶回身邊。幾年後
,巴鐸先生和蜜雪兒結了婚,一切漸漸穩定下來的時候,蜜雪兒卻應聘到了澳洲,巴鐸先生反正是個作家,住在哪裡都差不多,只要是講英語或法語的地方就可以了,所以也帶著馬克來,那時馬克十二歲。
難怪他看起來那麼不快樂,他有個不穩定、缺乏安全感的童年。
安德魯後來告訴我,馬克到了澳洲之後,朋友也不多,幾年前的一場戀愛,給他帶來短暫的甜蜜,但那位巴西來的漂亮女孩後來變心,愛上了一個南歐人,就離開澳洲了--唔,不幸的馬克。
巴鐸先生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,他說:「我告訴你這些事,並不是要你們同情馬克,而是像對一個好朋友那樣對待他,但別以為他的淡漠是故意的而生他的氣。我和蜜雪兒一直試著讓他快樂一點,可是他一向悶悶不樂,今天他似乎有點笑容,我想是因為他信任你和安德魯吧?他很少真心去交朋友......」
「也許他怕親密的朋友會離他而去,所以從不肯把心交出來吧?」
「我想你說得很對,」他看了看鐘,時間不早了:「我們換個話題吧,我們剛剛說到哪裡?檢查有沒有電子郵件是嗎?」 在巴鐸先生的書房,可以聽見遠處的濤聲,以及風奔馳在林間的呼嘯聲。這裡的光線不太充足,尤其到了晚上更是陰森森的——也許這是他刻意營造的氣氛,比較容易寫出恐怖的作品吧?
書房有很多書籍和雜誌,全是英文,因為雖然巴鐸先生的母語是法語,但他一直用英文寫作。這裡的恐怖小說反而不多,只有他自己寫的和編輯的而已。我翻了幾本,覺得還挺吸引人的,他說我喜歡的話可以帶回家看。
他特別給我看他上一本書的封面,問我覺得如何。那是碧綠的水面,有燈光或月光的反射,水面並不平靜,像是剛被投下一塊大石。但仔細一看,水面下竟然隱約有一張面孔,表情充滿怨恨……
「那是馬克的作品,很不錯吧?」他得意地說:「出版社非常喜歡他的作品,我下一本書還是會讓他幫我設計封面,他很能抓住我小說想要給人的感覺,畢竟他是我兒子。」 分配房間時,我選了書房隔壁的客房,因為如果我想去書房看書的話,又近又不會吵到別人。巴鐸先生的主臥室在頂樓,白天陽光從天窗照進來,一室的明亮。馬克的房間在二樓,不過他平常在雪梨市區附近和幾個同學分租一層公寓,只有假日才回來這裡。安德魯和莎拉選了馬克隔壁的客房,我則一個人留在樓下。
那天晚上,看了好一陣子書,明明已經很累了,我卻翻來覆去,無法入眠,總覺得身旁有人走來走去,有無數對眼睛在黑暗中窺視著我,而秋初的三月,夜晚不應該如此寒冷,為什麼我卻從背上一直涼起來呢?
難道我也受了巴鐸先生那些小說的影響,開始疑神疑鬼?
最後,我只好放棄入睡,張大眼睛瞪著天花板,直到撐不住了才入夢——夢境雜亂無章,我彷彿失去了形體,變成氣流,在風中飄飄盪盪,我穿過巴鐸先生的書房,看到新裝上去的數據機,幾個紅色小燈閃爍著,顯示正在接收傳真……我穿過關著的玻璃門,與無數和我一樣的氣流交錯而過,我想尖叫,才發現氣流是沒有能力尖叫的,我聽見呼嘯聲,但我又是如何能聽的呢?我覺得自己散了又聚,聚了又散——然後,清晨漸漸亮起的光線,從濃密的樹葉隙中透了進來……
第二天,我的眼圈免不了黑得像貓熊,只好跟他們說我會認床。安德魯和莎拉睡在樓上,他們看樣子也不是睡得很充足,可是那付卿卿我我的滿足模樣,和我這種被莫名其妙的恐怖感折騰了一夜的疲態完全不同,大概是晚上玩得太累了吧?馬克則低頭不語,偶爾看一眼餐桌對面的安德魯和莎拉,牽動嘴角,似笑非笑,不曉得是不是昨晚被吵到了?我忍不住想像,他們一定有個激情而甜蜜的美妙夜晚…… [下一頁]
(C)
Josephine Wu, All rights reserved. 未經作者同意請勿轉載或引用!!
|